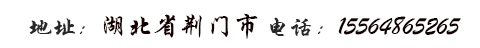赌鬼
|
民间有一类人,既不是算命风水先生,也不是道士法师,但却通晓阴阳,对术数有不俗的造诣,说来也有趣,这类人竟然是赌客...... 赌钱是个非常古老的行当,俗话说,十赌九输,按照现在的科学眼光来看,赌场里各种赔率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,参与赌博的人数越多,次数越频繁,赌场的利润越大,除此之外,还有出老千的、给富商下套的、合伙儿做局的,种种手段不一而足,客人只要进了赌场,往往都是血本无归,可偏有不少人不信邪,总觉得时机到了就能大赚一笔。 旧社会,赌场里的禁忌颇多,有人批量购买骰子,平时放在庙里供着,赌钱时拿出来用,希望受过香火的骰子能够扔出自己想要的点数;若是赌钱连续输,有人也会花钱把这骰子买下来,一锤砸个稀烂,要是发现这里面有灌水银,必是一场血雨腥风;也有人认为赌场里的各个数字与天干地支五行阴阳有些神秘的联系,专门钻研术数以研究其中的规律。赌场里尤其重视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,比如:在古老的哲学体系中,地支有六对冲的关系,分别是巳亥冲、寅申冲、辰戌冲、丑未冲、卯酉冲、子午冲,倘若属虎的客人被属猴的人拍了一下,必定认为是对方使邪术要借走自己的财运,非打起来不可,是以赌徒通常为了防止这一类的事发生,都要自己“学习”术数方面的知识。 那是清末的时候,湖南娄底有一家三口,当家的男人叫周邦宪,原家中排行老二。 寻常的百姓家,男人的名字大多简单好记,可这湖南娄底的名字就很有讲究,是指这块区域是娄星和氐星的交汇处,所以娄底的百姓家,就算自己没上过学不认得字,也往往会出钱请些有文化的举人、秀才,帮忙给孩子取个名字。 周邦宪这名,取自《诗经·小雅》,所谓“文武吉甫,万邦为宪”,这寓意不错,可周邦宪天生是个又懒又馋的家伙,天天往赌场里钻。 不知是祖坟冒了青烟还是什么缘故,周邦宪的老婆十分贤惠,平日里种田、操持家务,弄得井井有条,儿子周又喜刚九岁,也乖巧懂事。可老婆再能干,也经不住他三天两头地赌钱。每次进了赌场,不输得精光,他绝不肯出来。 这年腊月三十,一大早周邦宪就出门了,又是输了个干净才回家,这才发现家里连米和柴都没了。周又喜刚从隔壁三叔家回来,说三叔家里扣肉、肘子摆了一大桌,留他一起吃,孩子想起家里没有米没有柴,就算在三叔家吃饱了,爸妈也得挨饿,所以忍着饿就回家了。 周邦宪看孩子这么懂事,不禁有些心酸,可家里所有的钱今天已经输干净了,这会儿上哪弄吃的去呢? 想来想去,孩子妈心一狠,拿起剪刀把留了十多年的头发剪了,又把一条旧棉裤交给周邦宪,让他去卖了,换点钱做个年夜饭。 旧时,这长头发、旧衣服还能典当些钱,可得分两处去——旧棉裤可以直接去当铺当了,长头发只能站街边喊着卖,周邦宪图省事,想着赌场里但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有人收,虽说价格便宜了些,省得寒冬腊月里站在街头叫卖了。 一进赌场,坏事了,周邦宪把头发和棉裤换了钱,想着不如再赌一回,翻了本就能过个富裕年,却没想输了可怎么办,结果又输了个精光,顿时悔恨交加,没脸再回去面对老婆孩子。 家里周又喜和老娘等到天黑了也不见周邦宪回来,孩子的母亲没办法,去找邻居借了二斤米回来,娘俩熬稀粥喝了,又做了一碗干饭,想等他回家了吃。 可是一夜过去了,周邦宪的人影也没见着,孩子妈着急了,赶紧去赌场里找,从赌场的伙计那里打听到,昨天是有个人拿着一把长头发一条旧棉裤来换钱,然后没两圈就输干净了,总共也没待多久就走了。 孩子妈四处打听也没打听出周邦宪的下落,从初一到十五,周邦宪就像是消失了,她心里害怕周邦宪输了钱一时脸上挂不住,寻了短见,一得空就去找,一直到三月了还没见到人影。 这天,有俩放牛娃慌慌张张地来家里,对周邦宪的老婆结结巴巴地说,我们……看见周……周二叔在西山林里的歪……歪脖子树上吊死了! 她心里虽然早有这个推测,听到消息还是身子晃了晃,差点摔在地上,赶忙到隔壁,喊上周又喜的三叔,一起去西山林里找,可寻了一圈也没见到周邦宪的尸首。 孩子妈问道,你们说周二叔在这吊死了,人在哪里呢? 俩牧童里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个颤颤巍巍地说,刚才吓得忘说了,我俩见到二叔吊死在这歪脖子树上,吓得扭头就跑,跑了一阵子回头再看,就见那树上冒了一股黑烟,然后二叔就不见了! 这话说的挺玄乎,让人半信半疑,孩子妈登时就哭了起来。 小叔子安慰道,嫂子,别哭了,二哥他爱赌钱,不是个顾家的人,是死是活就由他去吧,咱们还得顾着怎么活,我给你垫些钱,你们娘俩做个小买卖吧。 二喜的妈说,我自从嫁过来,脚都没出过村子,我能做什么买卖呢? 小叔子说,不会做买卖,手上的活计能做吧?不如这样,你在家里做毛笔,我拿出去卖,你们娘俩只管做就好,其他的包在我身上。 孩子妈想了想,平时周邦宪虽然懒,但种地的活计没个男人还是不容易干,便一口应承下来,由小叔子出钱置办了些家伙,这毛笔作坊就算开起来了。 就这样,娘俩每日在作坊里干活,小叔子逢赶集的日子就带着周又喜一起出去卖毛笔,收了钱都交给侄儿揣着,晚上回家了还给嫂子报账,一年的功夫,攒了五吊钱,本钱也多了些。 这天,小叔子说,嫂子,这回咱们去苏杭二州做买卖吧,听说那边的读书人多,毛笔应该好卖,我带着又喜也能让他出去开开眼界。 又喜的妈说,这倒是个好去处,只是又喜还小,也没见过世面,去得远了,受惊吓怕是要掉魂,你不妨先去探探,走熟了再带又喜一起去,我们娘俩相依为命,要是他路上有个什么闪失,我可没法子活了。 小叔子一听顿觉有理,也不再强求,带上干粮行囊和毛笔直奔城东。 旧时的湖南到处是山地,交通多有阻碍,走水路是最方便的。娄底东边是涟水,直通湘江,坐船可以经长沙府换船,从湘江北上达武汉,再由武汉坐大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就能到扬州。 小叔子走走停停看看,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到扬州下了船,定下客店,就开始满城找商号问有没有要毛笔的。奇怪的是,各家店的掌柜一听他是卖毛笔的,都颇有兴趣,可拿来一看,问问价格,就摆手摇头说不要了。 小叔子没读过什么书,也很少出去走动,他哪里知道,浙江湖州是盛产毛笔的地方,全国各地的毛笔以湖州所产种类最丰、品质最优,又叫做“湖笔”,与徽墨、宣纸、端砚并称文房四宝。湖州当地人多以做湖笔为生,这湖州跟苏扬二州中间仅隔着一片太湖,乘船贸易往来十分便利。周又喜娘俩再心细,做毛笔如何赶得上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世家? 可各处商号的掌柜活计早已习以为常,不会跟他特别说明。惹得小叔子一肚子火无处可撒,气鼓鼓地收拾起行囊,准备去苏州再碰碰运气。 苏州离着扬州不远,路途平坦,就算不紧不慢地走,六七天的脚程也到了,小叔子见城里有一家二层楼的大店铺,便进了店铺,对伙计说,你们要不要毛笔?我这里有一批货,成色好,价钱便宜,我带了些样子。 伙计接过样品看了看,感觉虽然比不上湖州货,但做得也算精巧,说道,毛笔成色不错,但我说了不算,得问东家,你等一等。 不一会儿,那掌柜的出来了,小叔子迎上去,说,掌柜的,你看我这毛笔…… 还没等他说完,掌柜惊喜地说,呀,这不是三弟吗?! 小叔子抬头一瞧,顿时吓了一跳,原来这掌柜的不是别人,正是失踪了一年的周邦宪! 小叔子顿时喜不自胜,说,村里的人都说你输了钱,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,嫂子哭得死去活来,后来我跟嫂子侄子一起开了个毛笔作坊,她们娘俩做,我出来卖货,这一年里攒下了五吊钱,家里比之前好过多了。 周邦宪说,他们说这些坏话是糟蹋我,我好好的为什么要寻死呢?多亏兄弟你在家操持,这一年来辛苦你,哥哥感谢你,给你十两银子吧。 说着,周邦宪就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兄弟。 弟弟见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,对周邦宪说,哥哥客气了,只要你能走正道,做弟弟的心里就高兴,你离家这么远,一个人开店也不容易。 周邦宪说,实不相瞒,哥哥交了好运,生意越做越大,现时有六十多个伙计了。 说着说着,周邦宪哭了起来,接着说道,你嫂子和侄儿娘俩在家过苦日子,我心里难受,这一年过去了,又喜也不知长成什么样子了,让我想的紧,想回去看看,这么大一个店又放不下,你下次再来时,把又喜给我领来,在这里住些日子。 弟弟在这里住了三天,每日周邦宪都用好酒好肉招待,到第四天早上,弟弟说,哥,我该回去了,在外边时间长了,嫂子和又喜都惦记着。 周邦宪说,也好,你回去帮我给娘俩捎二十两银子,下次过来,千万把又喜带过来让我瞧瞧。 弟弟答应了,背上行囊去扬州坐船回娄底,一到码头,家也顾不上回,直奔嫂子家里,说道,嫂子,我见着我哥了,在苏州,他开了个大买卖,光伙计就有六十多人,还让我给你捎回来二十两银子,过几天我还去给他送货,他让我把又喜带去给他悄悄。 周又喜娘俩别提有多高兴了,原来家里这么一个只知道赌钱,没出息的人,现在走了正路,还知道挣钱顾家了。 二十两银子可不是小数,周又喜的娘拿这笔钱给三人都扯了布做新衣裳,又雇人把家里的破砖烂瓦都翻新了。周又喜整日催着三叔赶紧上路,好去苏州见周邦宪。 这小叔子一直等到嫂子的衣服做好了,才让周又喜穿上新衣裳,欢欢喜喜地出发,临走时孩子妈有些舍不得,百般叮嘱,把剩下的钱缝在周又喜的衣服里,让他路上花用。叔侄按原路坐船到扬州,再步行去苏州。 这天,叔侄俩在路上走着,见一个猎人手里提着一直刚抓到的狐狸,估计是要到苏州城里叫卖的。周又喜见狐狸挺可怜,央求三叔把它买下来。 小叔子不答应,周又喜自己把那衣缝撕开,拿出剩的银子交给猎户。猎户把狐狸交给周又喜,周又喜一松手就把狐狸给放了,气得小叔子直埋怨他乱花钱,哥哥辛辛苦苦在外面做生意,这孩子真是不懂事。 周又喜光听三叔唠叨,也不说话,低着头继续赶路。 俩人又走了一天,已经远远能见到苏州城的城墙了,小叔子突然想结手,让周又喜在原地等着不要乱跑,说完就去山坡后面了。 周又喜一个人在这荒地没事做,百无聊赖,突然见到不远处有只狐狸正在撒欢地跑,依稀像是前一天从猎户手里买的那只。 周又喜觉得这狐狸挺有趣,就跟在后面跑,这狐狸也奇怪,跑一阵就停下,回头看看周又喜,接着再跑。 也不知跑了多久,被面前一座破庙给挡住了,狐狸从墙角的一个洞里钻了进去,周又喜也推开庙门跟了进去,却见到庙里站着个大姑娘。 周又喜问道,大姐,你看到一只小红狐狸跑进来了没? 那姑娘说,你找它做什么? 周又喜说,我看它挺孤单,我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的也挺孤单,想找它玩一会儿。 姑娘又问,你这么个小孩子,一个人打算去哪里? 周又喜说,我爹在苏州城里有买卖,上回我三叔去苏州卖毛笔,见着我爹了,他让我三叔再去的时候带上我,他想我啦。 姑娘说,孩子,你晓得不,你爹不是人啊! 周又喜寻思这姑娘是说父亲之前整日赌钱,不做正经营生,便替父亲分辨道,我爹已经不去赌钱啦,他现时开个好大的买卖,光伙计就六十多人,还让我三叔捎了二十两银子回去。 姑娘叹了口气,认真地说,孩子,你弄错了,你爹现在身体是个人,魂灵是妖精,白天像人一样做买卖,晚上就去吃人,等他吃够一百个孩子,就成了鬼仙,到时候谁也治不了他了!他可不是想念你,是惦记着要吃你呢! 周又喜听着害怕,有些半信半疑,不知如何是好。 那姑娘见周又喜表情迟疑不决,说道,不瞒你说,你方才见到的那只小狐狸就是我,你前些天从猎户手里救了我,我是特地在这里等着你,来报恩的,绝不会骗你。 周又喜听罢,觉得这事实在是诡异,回想起之前的种种,先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周邦宪拿着头发和裤子出门了,接着就再也没了消息,那俩牧童说亲眼见到周邦宪上吊死的,尸体化作了一阵烟,不像是说谎。可三叔总不会认错人,带回家的银子也是真真切切的。周又喜心中想念爹爹,但又害怕万一真如这姑娘所说,爹爹已经化作厉鬼,一见面丢了性命可怎么办?姑娘的神情不似作伪,况且前几日买下狐狸的事,外人绝不可能知道。 周又喜心乱如麻,说道,这可怎么办,我不敢去苏州了,我这就让三叔带我回家去罢。 姑娘说,你爹要做鬼仙,吃的一百个孩子里头必须有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才行,不管你去不去苏州,就算走到天涯海角,他也要找到你。 周又喜吓得“哇”一声哭出来,跪下说,大姐,我该怎么办哇,求你救救我。 姑娘略一思索,从头上取了一枚金簪,递给周又喜,说,你把这金簪揣在怀里,要是遇见了什么危难,你摸一摸它就能逢凶化吉。 周又喜接过金簪放进兜里,给姑娘磕了三个响头,说,谢谢大姐! 姑娘忙把周又喜扶起来,说,别谢了,快起来,你这么半天没回去,你三叔该着急了。 周又喜问道,大姐,我以后上哪去还你这枚簪子呢? 姑娘说,不用你来找,等你十六岁和我长得一般高了,我去你家里取。 周又喜正要说什么,一抬头,见那姑娘突然消失了,连着身旁的破庙、院墙一起不见了,只剩下一片树林。 周又喜仔细辨认方向,回到方才的地方,三叔这时候也正好回来了,二人继续赶路。 又走了两日,这天傍晚快天黑了才到苏州城门,远远望见周邦宪正站在城门口候着,想必是提前算好了日子专程来接的。周邦宪见兄弟领着孩子来了,分外高兴,跑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周又喜,说,伢子你可算是来哒,想死我了。 周又喜想起那姑娘说的话来,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,又有些害怕,脸上显得不那么亲近。 周邦宪奇怪道,这孩子这是怎么了? 孩子的三叔赶紧打圆场,说道,怕是一年多没见,认生了,跟你多亲近几天就好了。 周邦宪便不再纠结,带着弟弟和儿子去了一家酒楼,点了许多酒肉,三人吃饱喝足,周邦宪背着孩子领着弟弟一起到城外的家里去住。 周又喜看爹爹的宅子很气派,但有一种阴森的感觉,偌大的宅院里见不到一点灯光,听不到丝毫人声,虽然爹爹在苏州没有亲戚,可这宅院连个佣人都没有,也太过诡异。 孩子的三叔喝了不少酒,这时有些迷迷糊糊的,也没察觉有什么不对劲。周邦宪把他领到一间卧房前,说,你今夜就睡这间,我和又喜一起睡。 孩子的三叔不疑有他,径自去屋里了,周邦宪背着周又喜还没走出多远就听见打呼噜的声音。 父子俩进了自己的卧房,周又喜趁着微弱的月光四处打量,总觉得这屋子十分恐怖,墙上隐隐约约有些发紫的血点。恐怕那狐狸大姐说的是真话,周又喜坐在床上战战兢兢的。 周邦宪以为孩子困了,就拉过被子来,父子二人躺在床上睡觉。 周又喜心里有事,怎么也睡不着,但又不敢动也不敢睁眼,就假装打呼噜。 到后半夜,只听见一阵大风刮过来,窗户响个不停。 周又喜忍不住偷偷掀开被子的缝隙往外看,这一看可吓坏了,只见周邦宪正披头散发龇牙咧嘴地站在地下,轻轻地问道,又喜,你睡了没? 周又喜更害怕了,赶紧闭上眼,假装把呼噜打得更响了,却听见周邦宪一阵尖笑,自言自语地说道,嘿嘿,睡得还挺沉,已经吃了九十七个了,还差三个,我再去抓俩孩子来,合着你们三个一起吃了,今天我就成了! 话音刚落,一阵风吹来,屋子里恢复了平静,周又喜继续装作打呼噜,等了一阵子,睁眼看去,屋子里只剩自己一个人了。 周又喜赶紧从床上下来,走出房门,闻到四处都是血腥味,吓得什么都忘了,只想着逃命,刚跑出宅院的大门去,突然想起三叔还在里面睡觉,又折返回来。 周又喜四处找寻三叔的那间屋子,找了半天也没找到,这时候听得树叶簌簌作响,又是一阵风,周邦宪回来了! 周又喜定睛一看,自己的亲爹简直没了人型,血红的舌头伸出老长,都快到心口了,张着血盆大口,那身体面的掌柜衣服不知为何变成了破布烂衫,一副阴森恐怖的模样,就像是听妈妈说的故事里那吊死鬼的长相。这恶鬼手里还抓着两个小孩子,俩孩子也不知是被吓晕了还是已经死了,闭着眼睛扔由它拖着。 周又喜这时躲在一旁,大气也不敢出,好在没被恶鬼发觉。 恶鬼将俩孩子拖进先前的卧房里,随手往地上一丢,就去掀床上的被子,不料周又喜早已逃跑了,一伸手摸了个空。 恶鬼自言自语地说,居然让他给跑了!不过我总能找到他,等我吃了这俩孩子再去找,逃不出我的手掌心!我成功就在今日了! 说完,它真就把俩孩子的衣服撕开,一使劲便把其中一个孩子的胳膊扯了下来。这孩子丝毫没有知觉,怕是已经死了。 周又喜看到这番景象,再也忍不住了,站起身撒腿就往外跑。 这一跑,恶鬼听见了声响,没顾上再继续吃这俩孩子,也追了出来。 周又喜顾不上回头看,只是没命地往前跑,跑了一阵子渐渐听得后面没有了声响,估计是已经把那恶鬼甩开了,便停下脚步大口喘气。 突然,一阵风刮过来,周又喜觉得浑身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,浑身直哆嗦,一眨眼的功夫,恶鬼已经站在面前! 周又喜吓得魂飞魄散,顿时脚一软就跪下了,哭着说,爹爹,我以后都听你的话,求你不要吃我了。 恶鬼说道,那可不成,我这一年费了多大的功夫才吃足九十七个,今天吃了你的心,我可就成鬼仙了,我也是没别的办法呀,你就可怜可怜我吧,乖孩子,爹爹最疼你了。 说罢,恶鬼上前来抓起周又喜的衣服前襟,把他拖在地上往回走。 周又喜跑了半天,这会儿又连连受惊吓,已经浑身瘫软,反抗不得了,只能任由恶鬼拖着,一边哭一边哀求。 恶鬼也不理他,脚下丝毫不停地往回走。 拖了不知多久,眼见又要回到那阴森的宅院,周又喜哭不出来了,见恶鬼不为所动,也冷静下来了,开始思索怎么脱身。 这时,地上有一块石头,恶鬼拖着周又喜从石头上过,一个趔趄,“叮当”一声响,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掉在地上,周又喜突然想起来,这便是先前那大姐送的金簪! 周又喜一伸手抓住了金簪,说来也怪,那恶鬼顿时就松了手,把周又喜扔在地上,退出十来步远,警惕地问道,你手里拿的什么玩意! 周又喜见它似乎害怕这金簪,便双手抓紧了,高高地举起来,只见一道金光从簪子里飞出来,直奔恶鬼的胸口。 金光去速甚快,恶鬼毫无防备便被这道金光贯胸而过,连声音都没出就仰头栽倒了。 周又喜等了一会儿,见恶鬼躺在地上不动弹,大起胆子来走近了,却看见恶鬼身子化成了一滩血水,臭味飘散开来,令人恶心不已。 这时候周又喜才回过神,想起三叔还在屋子里,便又回到宅院,碰巧三叔正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撒尿。 三叔看到周又喜浑身都是土,衣服也扯破了,酒醒了大半,问他怎么回事。 周又喜说,那个不是我爹爹,它是个恶鬼,咱们快跑! 三叔还没反应过来,周又喜便拉着他的衣服往外拽,三叔忙说,我衣服还在屋里墙上挂着呢。 说罢就倒拉着侄子往屋里去,没走两步,只听得远处几声鸡鸣,眼前的豪华宅院消失得无影无踪,变成了一座挨一座的坟头,这做叔的顿时清醒了过来,再回头一看,自己的衣服正挂在一棵歪脖子树上。 这下三叔知道周又喜所说是实,连忙穿好了衣服就带着周又喜离开了坟地。 二人不敢再去苏州,没日没夜地赶路回到扬州,才定了客店住下休息一日。周又喜得空把那日如何遇见了大姐,大姐跟他讲他爹爹已经化作厉鬼,又送给他护身保命的金簪,以及半夜里爹爹现了原形去抓孩子吃的情形,从头到尾细细跟三叔说了。 二人直呼庆幸,要不是先前周又喜买了那只狐狸,这会儿怕是已经进了恶鬼的肚子。 三叔带周又喜坐船回了娄底,把事情的原委跟孩子妈也说了,气得她破口大骂,这周邦宪活着的时候不知道顾家,死了化作厉鬼还要吃自己的亲骨肉,实在禽兽不如,从此只当没有这么个人,再也不曾提起过。 后来,周又喜娘俩继续做毛笔,做了五年,攒了不少本钱,在城里开了个商铺,周又喜做起了少掌柜的。 到周又喜十六岁那年,孩子妈请媒人说亲,给孩子办婚。 洞房花烛夜,周又喜掀开新娘的红盖头,发现妻子不是别人,竟是自己五年前在苏州城外遇见的大姐! 妻子杏眼圆睁,纤手一伸,向周又喜问道,我的金簪呢? ▲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hulua.com/xedhl/1040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经常入睡困难,半夜惊醒,一个两味药方,扑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