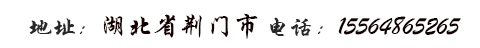耳边响起呼噜声
|
近两年,我的睡眠质量明显下降,尤其是在准备睡觉时听到别的声音,更是难以入睡。然而,不知从何时起,老李在睡觉中打起了呼噜。有时我刚躺下,他的呼噜声骤起。我轻轻拍下他,只能换来片刻的宁静。往往在我刚进入迷糊状态时,他的鼾声又起。一夜如此反复多次,让我苦不堪言。 按照医生的说法,打呼噜是一种疾病,可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,造成大脑血液缺氧,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。但是,不少打呼噜者对此并不在意,仿佛睡觉时打呼噜,反能证明睡得很香。 前年暑假回老家,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看电视,父亲坐在靠椅上。他明明已经很困,却不肯到床上睡觉。正当我们陶醉在剧情之中,父亲的鼾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 父亲的呼噜声很大,拖着长长的尾音,似乎吸气后很久方吐出来,听到的人就好像心脏被提起来半天才放了下去。因而,听父亲打呼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。 当晚,我和母亲睡在里间,父亲睡在外面。因为临时安置房的空间狭小,又不隔音,父亲的呼噜声显得格外响亮。当我躺在床上无聊地数着“一只羊、两只羊”的时候,不由地想起两年前的夏天,我和老李因为不能忍受呼噜声而被迫睡在车里的情景。 我已记不得小时候和父母睡一个房间时,是否听到过父亲的呼噜声。印象中父亲的呼噜声总是伴随着电视响起的。他那时辛苦劳作一天,晚饭后和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,往往在新闻联播过后,电视剧刚开始,父亲的呼噜声就响了起来。 母亲常常推推父亲的肩膀,提醒他到房间里睡。他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,嘴里说着“我没睡着”,之后又半睁着眼睛盯着电视。谁知不到两分钟,他的呼噜声再次响起。我们在一旁就会哈哈大笑。 我在高三复读时,宿舍里有一个女生打呼噜。偏偏另一名女生的睡眠质量很差,我只知道她总在熄灯后从上铺爬下来去厕所,并不知她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可以想见,那名打呼噜的女生对她来说是多大的折磨。 及至舍友找到我联合签名,要求宿管办把打呼噜的女生调走时,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。因为每天晚自习结束已接近10点,回到宿舍我在匆忙洗漱后倒头便睡,从未操心他人的动向。此时,我方后知后觉宿舍里有人打呼噜。 医院住院时,我们趁端午节放假前去看他。到了晚上,医院附近找了一家洗浴中心,洗浴后就在那里休息。不曾想,洗浴中心的生意很兴隆,有很多人和我们的想法一致。 一个约二百平方米的大厅里,摆放了许多沙发床,洗浴的人换上浴衣在里面休息,看电视、嗑瓜子或者睡觉。刚开始,还能听到聊天的窃窃私语声,12点过后就只剩下一种声音了。 各种各样的打鼾声响作一片,此起彼伏。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。有的声音似吼叫,有的声音长而尖利,有的吸气声短促呼气时拖着长腔,有的吸气声很长呼气时却戛然而止。 那时没有智能手机,我的手头又没有书。我备受煎熬地躺在那里,越想入睡,越被呼噜声所困扰。无奈,只得一边在心里默默分辨哪个呼噜声是男人还是女人的,一边盼着尽快天亮。 我家的电视机连上WiFi后,老李培养了新爱好——追剧。他从在电视网络上找节目,发展到用手机投屏,连午休地点也换在了沙发上。每天从葛优躺到侧躺或平躺,及至呼噜声响起,电视节目仍在播放。 我有时以为他已经入睡,一边抱怨他浪费电,一边抬手去关电视。我还未到电视机前,他就有了反应,立刻停止了打呼噜,告诉我他在听电视。我表示不解,反问:“你在睡梦中听吗?”但他非常肯定地强调“根本没睡着”。 有一次,老李告诉我“听见了自己的呼噜声”。我对此感到很奇怪:他明明已经睡着了,怎么能听到自己的呼噜声呢?他却说确实听到了自己打呼噜的声音。这让我颇为不解。 我从网上查看了打呼噜的原因,对照老李加以归纳。直接原因有二:一是他多年的慢性鼻炎所致,二是机能性问题。比如,他在仰卧时更容易打鼾。此外,抽烟和喝酒则是引起他打呼噜的间接因素。他每每在饮酒后,呼噜声更加频繁。 厚夫在《路遥传》一书中曾描写过路遥的呼噜声——即使门窗均关闭,凡是从他门口经过的人,无不听到从里面传出的如雷的鼾声。作家贾平凹曾经因为开会和路遥住在一个房间,被路遥的呼噜声折磨得彻夜未眠,说他“是大人物,只能一个人住”。路遥本人对他的打鼾并不以为意,最终却因肝硬化英年早逝。 近日,我看到北京卫视的一段节目视频。先由三名演员分别表演了三种不同的打呼噜状态——声音粗且持续不断、声音细且持续不断、声音粗但中间有间歇。之后,医学专家指出第三种打呼噜最为危险,容易导致夜间猝死。 看来,小病不容小觑。在我们的生活中,有很多人因为忽视小病,最终酿成了大患。打呼噜尽管常见,还是应该早早治愈。 李现森|像狗一样地活下去 李现森|偏方 李现森|前进的“街灯” 李现森|拉脚儿 冬日里的“春天故事” —政策资讯 赏文 赏艺 赏思—牛永超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hulua.com/dhzlff/673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人到中年,当你感觉白天嗜睡要当心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