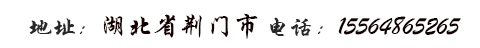回乡散记
|
北京看白癜风最好的地方 https://m-mip.39.net/baidianfeng/mipso_4227336.html 又回老家了,回去喝喜酒。十三爷爷的二孙女、也就是我小叔的大女儿,四月十一结婚,初六小叔请喜酒。 我喜欢回老家喝喜酒,热闹,亲。族里的人,嫁出去的闺女,娶回来的媳妇,亲朋好友,东邻西舍,能来的都来了,挤挤巴巴一屋,窜来跳去,喜笑颜开,叽叽喳喳,吃饭不是主要的,拉呱儿要紧。现今谁还缺顿饭啊?喜酒就是个引子,人们借这个由头聚一聚,拉一拉,解相思,叙亲情。 初二,三姐说,是不是你记错了日子,我怎么看着咱小叔请喜酒了?三姐看到堂嫂发的抖音,说小叔家大妹妹结婚,小叔请客,全家人聚一起真乐呵。我说不对吧,我在台历上记着,怎么会错啊?我们又看了几遍抖音,数了数人头,发现二嬢嬢也在。二嬢嬢七十多了,腰弓得厉害,自己总说没个人样儿了,见不上人了,一般场合都不去。我说咱小叔这回请客请得真彻底,连二嬢嬢都出动了。打电话给堂嫂,她说大妹婆家来下礼,小叔找人陪客,老王家在家的都去了,三十多口子。 这是老家的风俗,闺女要出门子,婆家来下礼,娘家就要请德高望重的族人来陪客。这些年在老家的人少了,生活也好了,每逢这种喜事儿,也不分什么德高望重了,家族里只要能动的,全都去陪。请客的不差那俩钱,陪客的也不差那口饭,大家伙儿就是凑上块儿热闹热闹。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现在孩子少了,借这个事,凑这个场,也是为了让婆家看看,看看媳妇娘家不是独门独户的小人家,而是人强马壮的大户。?? 这个风俗由来已久,但有个阶段好像不大重视了。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。那个阶段,大家都全力抓经济,好像除了钱其他什么都不重要,什么都不顾得。经济是实质,其他都是形式。我们忽略一切形式直奔实质。不独我老家,全国都这样。这些年,人们手头宽裕了,也慢慢意识到人、人际和谐才是最重要的。谁说农民觉悟低?谁说农民没有精神追求?他们不会说罢了。 我从小爱热闹,找算嫂子们:“这种好事儿你们怎么不叫我呃?现在这个社会还有偷吃的东西?你们谁吃的、吃的什么,我数得一清二楚。”她们嗤嗤笑。我说偷吃了东西还好意思笑! 三姐原先不爱热闹,上了年纪也爱凑热闹了。她看孙女,可是不去她心里痒痒,就叫儿媳妇请假看孩子,我们领着老娘,回老家,喝喜酒! 小叔请喜酒找了个好日子,初六,石门集,赶完集直接去喝喜酒,多好啊。我们正好顺带赶集。农村长大的人谁不爱赶集啊? 石门集原本就不大,近些年越发小,成了“老婆集”了——一到天晌做饭的时候就散了。我们带着任务赶集。三姐儿子从小爱吃石门集上的烤鸡皮,来了日照也念念不忘。他媳妇天天听他念叨,不知烤鸡皮是何等人间至美,命令婆婆务必买回来。 刚到集口,三姐和母亲就拉不动腿了——碰到熟人了,接二连三的熟人,拉不完了。我催了又催,她们半天挪了二指。烧肉摊子好几个,都没有鸡皮。问道怎么不烤鸡皮了?回答说太费事了,得一根一根地拔毛儿,没有大功夫弄不了。怕三姐完不成任务,我拉着她又走了街里两个烧肉店,都没有烤鸡皮。火烧还有,可是这次不想买了,上回买多了。三姐买了油条。石门集上的油条和日照的不一样。母亲和三姐吃不惯日照的油条,说没炸透,中间有死面,炸透了的也没个油条味儿,还是老家的油条好吃。 又买了青菜,扁豆、土豆、西红柿。别说我非得回老家买菜吗?我跟你说,不一样。日照市场上买不到我们老家的扁豆。老家人爱吃爱种青扁豆——一种肉厚豆肥、老青色的扁豆。我也爱吃,回诸城、回石门碰到就买,今年干脆从二嫂家拿了种子自己种了。老家人至今把西红柿叫洋柿子。南丁家庄人种菜,石门集上卖菜的多数是那庄的。他们种的洋柿子七大八小,在太阳底下都粉丹丹的,一看就面齁齁、一下能掰开的样子。 赶完集十一点刚露头儿,窜到饭店,心想怎么也是第一名。结果不是,有赶完集的邻居早来了,二叔和一个堂哥忙着往桌上摆烟酒。刚坐下,小叔雇的客车第一趟也到了,从村里拉来一车喝喜酒的。不久第二车也来了,整个大厅立即沸腾了。 去年喝侄子大帅的喜酒,回来说给大连的小伙伴,她说坤娟以后再有这种事你一定录个视频哈,给我看看,我真想咱庄里的人呃。我挨桌录了几个视频,发给她。其实一些人我也不认得,她们是我离开村庄后嫁来的,别人给我介绍,说这是谁谁谁他媳妇儿。可是人这么多,我转头就忘了。倒是以前认识的现在不认识了,别人说这不是谁谁谁吗,你忘了?稍一端详,立马就想起来他年轻时的样子了,看看那眉眼,其实也没大变,就是老了。我录视频,他们都笑着说,别录了,都老得没点人样儿了,谁稀看呃?我说别人不稀看,从小在咱庄长大的人爱看。他们就笑得眯缝着眼,展着一张张晒得黢黑通红的脸。我爱这些脸,从心底觉得亲。 石门的饭菜不用多说了,全是硬棒菜。我老公是彻头彻尾的吃货,嘴尖毛长,可是对我老家的饭菜,除了咸,他挑不出毛病来。他对我老家人总体评价是“实在”,说做饭也实在,都是深盘大碗,一盆子一盆子地上。别以为我老家人肚子大、能吃,现在谁都不缺肚子了,松开腰带也吃不完。也别说我老家人浪费。每分钱都是一个汗珠子甩八瓣儿挣的,他们还没学会浪费。让人家吃饱吃好是农民惯有的待客礼道,菜好量大也是饭店开下去的保证。 我最喜欢老家宴席上的烤猪脸,喷香,筋道,又好看。对我来说有点咸,可是咸就咸吧,又不顿顿吃,吃完多喝水就是了,活得太在乎就没意思了。同桌堂嫂问我日照的婚宴怎么样。我腾出嘴来,说,白搭,连咱这里一半的都没有。这盆蛤蜊顿蛋在日照能盛五盘!山药炖排骨在日照谁舍得放这么多排骨?大妹在青岛结婚,堂哥堂嫂们过几天还要去青岛婚宴现场喝喜酒。青岛婚宴高档中档我都吃过,同我们老家相比,也白搭。我说你们抓紧吃呃,别以为去青岛能吃什么好东西,捎着眼看看就中了。 饭吃得差不多了,人们下桌窜位耍,各人找自己想念的想耍的。有两个找我母亲耍的“年轻人”叫我很动感情。 一个是我家河南崖老邻居的小女儿,四十出头,小时候都叫她二嫚儿。她父亲是我一年级老师,齁,一到冬天出不来屋,整天挓挲着手蹲在炉子跟前烤火,齁啦齁啦喘得像风箱。后来一口气上不来,憋死了,至今二十多年了。她姐姐叫大嫚儿,是我小伙伴,25岁肠癌去世了。她母亲头脑不利落,干不了细活儿,连两个闺女的生日都记不住,隔阵子就跑来问我母亲:“二嫂子,俺大嫚儿多咱生日来?”“俺二嫚儿多咱生日来?”我母亲就告诉一遍。可她仍然记不住,过阵子再来问,直到生日前我母亲提醒她。二嫚儿从小各方面不如大嫚儿,虽然父亲是老师,可没叫她上学,就在地里干活儿,长大后嫁到邻村。老家人说二嫚儿真能干,小日子过得奇好。二嫚儿娘我们叫二婶子,改嫁去了土屋村。我母亲想她,经常念叨她,前年叫我妹妹拉着去看她,回来说,恁二婶子找这个老汉儿不孬呃,对她奇好。(她)一辈子吃齁厮(指二嫚儿爹)的气,这回算是享福了。看了她们的照片,我高兴得流泪,打算抽时间去看看她。我也想她啊。 二嫚儿一进大厅,就跑上来拉着我母亲,不住地喊“二字娘”。别看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总是笑嘻嘻地答应着,其实很多时候她根本不认得对方是谁。我跟二嫚儿使眼色,问母亲她是谁?母亲高兴地瞅我一眼,笑哈哈地拉着二嫚儿,说:“这不是南崖俺二嫚儿嘛。”席前我挨个桌打招呼,二嫚儿一把拉住我,说,四姐,俺娘没有了,死了十来天了。我简单问了问,拍拍她肩膀,其实心里极难受,我还没去看二婶子呢。 饭后二嫚儿又过来找我母亲,叫我母亲到她家住下,翻着手机叫我们看她新添的外孙,然后又拉过来她男人,逼着他叫我母亲叫娘,说,这就是俺娘呃,我小时候对我那个好呃。你快叫娘!二嫚儿从小直爽,说话咋咋呼呼,可是说着她就红了眼眶。我也红了眼眶。我知道她刚失去娘,心里难受,我母亲给过她温暖,她不自觉地就在这温暖里寻找寄托。 还有一个叫孙乐菊,是我家西边邻居的闺女。她父亲极老实,没什么本事,也没大力气,爱喝点酒扛着枪打兔子。她母亲精神也不利索,还齁。她哥哥跟我同岁,智障。孙乐菊从小洗衣做饭拾掇家。为了顾家,她又嫁在本村。她小时候瘦小,我担心地里的活儿她怎么受得了。那几年问三姐,三姐说,人家孙乐菊现在不是一般的能干,牲畜没少养,地也没少种,男人还出去打工,日子过得登登的,现在买楼她也不愁。今年,三姐经常拿着抖音叫我看,说,你看看孙乐菊,能煞了,也不识个字,抖音耍得突突的。我母亲也爱看她的抖音,看见她就笑得满脸开花。 孙乐菊叫我母亲二嫂子,搂着我母亲的脖子贴着脸亲,说想煞她了。说我母亲太瘦了,要抱起她试试多么沉。我真感动。乡邻间的感情,跨越血缘,历久弥坚。二嫚儿和孙乐菊都大字不识,如今都身形壮实,儿女双全,都用双手用汗水扎扎实实地把日子过起来了。真替她们高兴! 饭后,别人都走了,也不用小叔小婶吩咐,堂嫂、弟媳们自动打包、收拾东西,搬到车上拉回小叔家,各人就走了,忙着上坡抠花生。今年雨水足,墒情好,花生出得齐刷刷的。不及时从膜里抠出来,几天就憋毁了。花生是经济作物,乡亲们都种了十几亩、二十几亩,这几天从早晨五点到夜里八点都蹲在坡里,一棵一棵地抠花生。 我们到小叔家拿了喜果子。我和三姐是出了门子的闺女,回来就是客,各人一份喜果子,这也是老风俗。 二嫂早领着母亲去看她的新屋了,我们也得去看看。 我大爷四儿两女,如今只有二哥在家。二哥七十岁了,两个闺女都在城里做生意,各家几套楼。俩闺女这些年总是试图说服爹娘去城里,随便挑她们的楼住。二嫂死活不去,说哪里也不如老家,还是住她的小屋心里踏实。侄女跟我抱怨,叫我劝劝她娘。我说就随他们的便吧,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。有些事不到一定年龄不明白。我经历过了,侄女还年轻,还不能理解她们父母对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和老屋的感情。 可是二哥的老屋确实不济了,小,返潮。快五十年的老屋怎么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呢?俩侄女下了通牒:要么上城里,要么翻盖老屋。二哥二嫂选择翻盖老屋。老屋翻盖工程量多大啊。我真替二哥二嫂愁得慌。他们也愁。侄女建议不如买别人的屋吧。二哥二嫂不,住了一辈子的老地方,他们舍不得。从三月十二动工,四五天前毛坯完工,等着晾干后再继续拾掇。 回日照,我决定走东路,顺带送大姑、看大娘。 这个大姑是十二爷爷的大闺女,嫁到石河头村。我很小就知道,但这是第一次见。我记事儿前大姑就出嫁了,上了东北,后来又回来的。大姑说我下生没几天,赶上我爷爷的五七坟,我父亲趴在坟上放了声,哭得她们都拉不起来。说头一回见我父亲那么哭。说四嫚儿你想想,那个年头儿一连仨闺女,到了你谁不巴个儿呃? 几年前有人在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hulua.com/dhlyy/807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你听说过孝子产业链吗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